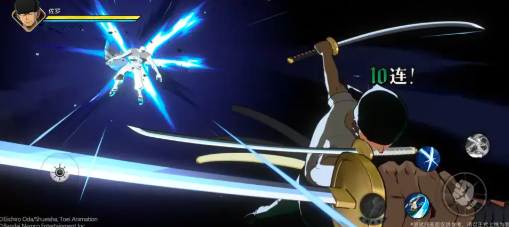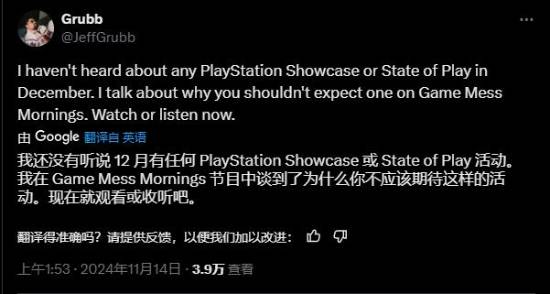浩瀚的宇宙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历经了几十亿年,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在地球第五次生物大灭绝之后开始的。 在六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的进化经历了质的变化。 直到今天,被冠以“人类世界”之名的纪元,我们似乎真的成了地球的统治者,但殊不知依然要经历各种天灾人祸。
没有人对自然的威力感到惊讶,却往往疏于对生灵的恐惧。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非典,直到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的噩梦。 其实回顾历史,人类不过是一场兜风,天花、流感、疟疾、鼠疫、麻疹、霍乱……瘟疫一直没有远去,不幸成为亲人,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的碎片。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容易产生很多关于人性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镜像,今天只是昨天的影子,我们面临着和过去一样的危机和恐慌。 过去,就在那些作家的笔下。 在不同但共性的疫情情况下,个人选择、情感关系、群体失控被无限放大、最终记录,引发长期思考的是人性的善恶、情感的复杂性、个人命运的无常。
作为镜像的鼠疫
说起瘟疫相关的作品,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无疑是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暴发真正的鼠疫是在公元54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黑死病”的袭击,第三次是在十九世纪末,起源于中国云南省,影响世界,持续了半个世纪。 其中,1910年哈尔滨的鼠疫事件,是因为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所以对历史的详细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
《鼠疫》
在众多的瘟疫事件中,鼠疫的激烈、反复、沉重对人类进程的影响极其深刻,这一切都导致了加缪的创作。 《鼠疫》无疑成为瘟疫题材作品中不可替代的文学名作,再现了面对瘟疫时人性的种种面相,可见经历瘟疫的我们与之相似。
(加缪( 1913~1960 ) )。
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法属北非沿岸城市阿夫兰。 那里有20万人口,没有臆测和色彩,平凡而麻木,人们拼命追赶钱,几乎不去想。 在春天到来之前,不可避免的瘟疫打乱了城市就业的节奏。
意外的是,每当疫情袭来,站在最前线的总是医务人员,他们是最先感知到疫情信号的人,也是减灾的战士。 在《鼠疫》中,一位利亚医生结束了整个故事。 当他走出诊所,在楼梯间第一次发现死老鼠时,预示着阿夫兰这座城市将陷入无限的恐慌。
瘟疫愈演愈烈,经历了城市封锁、人们意想不到的紧张不安的过程,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逃了,有的人逃了,有的人——其实,我们也一样,或者说,不管什么时代,哪个地区的人都在灾难面前表现得很好加缪在书中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一直奋战在一线的李奥医生和组成防疫志愿者队的医生、护士们,记录疫情,积极参与城市救治的政治家,为逃离城市而最终参加志愿者的外国记者, 贫穷却要承担防疫重要工作的公务员,宣扬鼠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的神甫,因失去儿子而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的法官,如鱼得水的罪犯,国难致富的商人,为高贵人士斡旋的经纪人,醉酒的人,流浪的人瘟疫面前没有区别,又各有不同,在变幻莫测的死亡和灾难中的不同选择,几乎尽了灾难中人性的无数可能。
像镜像一样,过去映射着我们的现在,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人都是无知愚蠢的。 就像书的结尾一样,瘟疫结束后,听到街上的欢呼声,利亚老师说:“鼠疫菌永远不会死,也不会消失……总有一天,鼠疫会再次唤醒它的鼠群,埋葬在幸福的城市,让人们再次遭殃,吸取教训当然,我现在知道永远不死的不仅仅是鼠疫,还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瘟疫本身。 希望同样经历过这些灾难的我们,在疫情过后,能够从中真正吸取教训,而不是仅仅欢呼。
盲流感背后的人性下沉
如果说加缪的《鼠疫》写尽了瘟疫带来的暂时现实和个人痛苦,那么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则通过寓言的形式紧追人性,通过群体的沉沦,撕破文明的外衣,揭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
( 651《失明症漫记》作者萨拉马戈( 1922~2010 ) )。
小说是从突然的白色瘟疫开始的。 一名开车的日本人突然失明,成为了0号患者。 随后,送他回家帮助的偷车贼、他去看病时接诊的医生和诊所的其他患者相继失明,无缘无故的瘟疫蔓延。 再次以医生为中心,他以敏锐的职业素养判断这可能是具有传染性的流感,并迅速向政府发出了信号。 而且,这场“盲流感”也在以迅速的速度扩散。 对此,国家的解决办法是集体隔离感染者。 于是,这些相互交汇的首批患者在精神病院临时搭建的隔离区再次重逢。
看起来没有生命危险的失明,使人类失去了文明的外衣。 政府没有派人去照顾这些失明者,而是让他们自我驱逐。 恐惧侵蚀着人性的道德,欲望侵蚀着人类的理性,在失去尊严的黑暗中,被抛弃的人们又回到了动物的原始状态,猜疑、争夺、欺凌、杀戮,宛如人间的炼狱。 这是对这个世界绝望的萨拉马戈,是人类最锋利的鞭子。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样的困境,但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总是在现实中重演,出现在瘟疫还是其他形式。 “有赖”对人类的健忘视而不见,它会发生在过去,在未来重新启动吧。
《失明症漫记》
“如果能看到,就必须看到。 如果能看到,就要仔细观察。”萨拉马戈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唤醒人们的意识。 就像书中他设置了唯一没有失明的——医生的妻子,就像故事结尾盲流突然消失一样,作者虽然是个“愤怒”的人,但始终抱有希望。 瘟疫的可怕来自人心,而人心的觉醒来自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清醒认知。 人类从来没有失去过光。 他们失去的只是大脑的认知能力。 当眼睛变成动物般的工具,不再是大脑传递精神信号的中枢时,失明的瘟疫一定会卷土重来。
爱也是瘟疫
与《鼠疫》的现实主义和《失明症漫记》的寓言风格不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选择了浪漫主义的方向。 它与瘟疫有关,与感情紧密相连。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风靡全球,《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仅次于《百年孤独》的知名度代表作,讲述了一个半世纪的爱情故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 1927~2014 ) )。
这个故事设定在19世纪的80年代到20世纪的30年代之间。 哥伦比亚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不是霍乱,而是“千日战争”这场内战,但在小说中瘟疫贯穿了整个作品。 但是,它并没有带来集体的恐慌,而是成为了爱的纽带。 在这里霍乱是比喻性的。
新闻记者艾丽莎和少女费米娜深爱着青春的年轻,但由于看门的关系被女性的父亲撕裂了。 之后,因为瘟疫,费米娜认识了医生乌尔比诺,开始步入人生的“正规”,和他携手结婚。 正如乌尔比诺所说:“爱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为了安定体面的生活,有人会在动荡中选择远离霍乱,也有人会身败名裂。
但是艾莉莎没有忘记费米娜,她有622个恋人,但费米娜相信这是自己唯一的爱。 直到乌尔比诺去世,和费米娜分手53年7个月11天后,两个老人再次在一起。
马尔克斯这部讨论爱情的作品一直备受争议,有人感动,也有人鄙视,小说里的爱情有深厚的感情,也有滥交; 有初恋,也有婚外恋,还有各种各样的禁忌,让很多人感到困惑,这也是霍乱的隐喻。 瘟疫时代,瘟疫般的爱情,让艾莉莎陷入了自制的病毒。 但就像病毒一样,在人类众多的感情中,爱是最失控的。
用瘟疫释放爱,马尔克斯将爱的百态写尽,远离理性和道德,有时也有瘟疫般的爱。
从《鼠疫》对社会个体的关注,到《失明症漫记》对人性的深刻批判,到《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人类情感的深刻诠释,再到同一场瘟疫的题材,三位作家以不同的风格和视角写下了不同的故事。
加缪试图通过还原瘟疫时期的场景,用哲学思想来警示人们,萨拉马戈试图引发瘟疫灾难,以寓言方式唤醒人们的意识; 马尔克斯是瘟疫的隐喻,他试图用宏大的叙事诗揭示爱情的本质。
当然,除了这三部名著之外,还有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池莉的《霍乱之乱》、前文迟建的000等瘟疫题材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或者身处其中的我们,在瘟疫蔓延的时代,除了恐慌之外,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生命的意义。 ( (折篇(张玉瑶) ) ) ) ) ) ) ) ) ) ) ) ) ) )0)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张艾因
编辑:袁新雨
流程编辑:吴越









![大将军[清软]完结下载_大将军[清软]完结2022最新破解版(今日已更新)](/uploads/2022/08/0802103301554.png)